愈见你 | 与双相共处的日子:在情绪的浪涛里锚定生活
编者按:在人类漫长的生命旅程中,健康与疾病始终如影随形。每一次关于疼痛与疗愈的记录,都成为人性、希望、坚韧与爱的深刻展现。而放眼未来,我们预见的不只是医疗技术的惊人飞跃,更是对病患愈发深切地理解与尊重。医学的终极使命,不是对抗自然,而是在敬畏中寻求精妙干预,在理解中维护动态平衡,与人类本身的复杂性共舞。本文为《身体周刊》读者投稿的患者故事,“愈见你”,感受生活的点滴。我是在医生的电脑里才第一次看清楚自己牙齿全貌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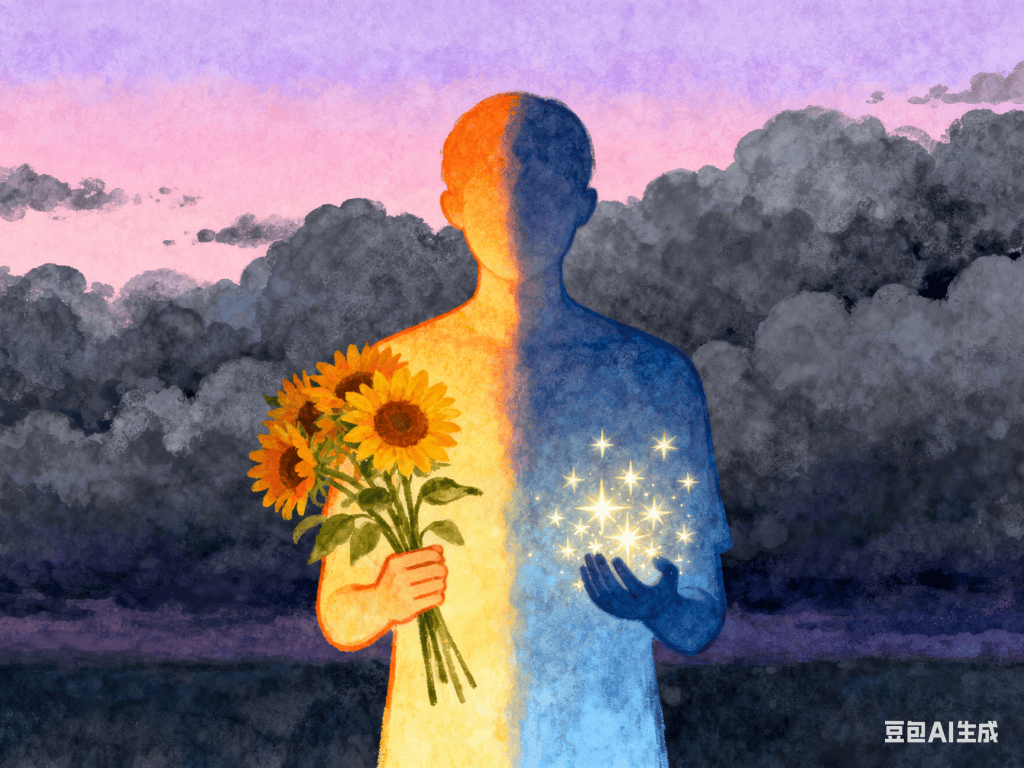
清晨五点半的莒南汽车站,广播里循环的安全须知像老式座钟的摆锤,敲打着我混沌的神经。数完最后一张零钞,指节无意识地在售票台上叩击——这是吃了十五年丙戊酸钠的后遗症,也是我确认自己活在真实世界里的方式。玻璃窗外,蓝色大巴车的雨痕未干,像极了那些洇湿稿纸的深夜泪痕。
风暴降临的清晨
2010年春天的失眠来得毫无征兆。整夜盯着天花板时,脑子像装了永动机,各种念头翻涌不息;白天却亢奋得异常,给乘客讲笑话手舞足蹈,收票时屡次多找钱也毫不在意,甚至觉得"钱乃身外之物"。可深夜总会坠入谷底,坐在床边看黑暗吞噬一切,活着像件荒诞的苦差事。
妻子最先发现异常,她眼底的红血丝一天天加重,轻声劝我去医院。我却像被踩了尾巴的猫,暴躁地摔了搪瓷杯:“我没病!”瓷片四溅时,她眼里的光瞬间熄灭,蹲下去收拾碎片的肩膀微微颤抖。那刻心口被针扎似的疼,骄傲和恐惧却像两只猛兽,在胸腔里撕咬着不肯退让。
五月的那个清晨,灾难终于爆发。售票台后的数字突然旋转,耳朵里嗡嗡作响,乘客的说话声尖锐得像玻璃摩擦。我想抓住桌沿,手指却不听使唤,直挺挺瘫坐在地。意识模糊前,“他是不是疯了”的尖叫像冰锥,狠狠扎进混沌的脑海。
再次醒来是刺眼的白光和消毒水味。张医生递来的镜子里,男人眼窝深陷,胡茬疯长,眼神浑浊得像泥潭。“双相情感障碍Ⅱ型”,诊断书上的字被阳光照得发烫。“情绪的过山车,时而躁狂,时而抑郁,需要终身服药。”这八个字砸下来时,我捂着脸蹲在地上,压抑许久的恐惧、委屈、无助全化作呜咽,在病房里撞来撞去。
戴着枷锁的生活
住院的日子像场漫长的噩梦。躁期发作时,我在病房里踱步,对着墙壁滔滔不绝讲客运线路,直到嗓子嘶哑还停不下来。护士来打针镇静,我像受惊的野兽般反抗,被按住时的嘶吼里全是绝望。郁期来时又陷入另一个极端,整天躺在床上,连妻子握着我的手都毫无知觉。她讲女儿晓雯的考试成绩,讲大巴车的近况,哽咽的声音是黑暗中唯一的光。
出院那天,丙戊酸钠的塑料外壳硌得手心生疼。走出医院,行人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身上,我下意识把药盒藏进衣兜,仿佛那是见不得人的秘密。刚开始吃药比晕车难受百倍,手抖得握不住方向盘,开着车会突然犯困,国道上那次差点追尾的刹车声,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
病耻感像件潮湿的棉袄,裹得人喘不过气。跑车时总戴顶压得很低的帽子,去医院拿药绕着正门走侧门,药瓶藏在驾驶室工具箱最深处,还特意撕掉标签换成维生素瓶。碰到同跑客运的马三强时,他阴阳怪气的笑让我攥紧药盒转身就走,后背全是冷汗,心脏狂跳得像要冲出胸腔。
最痛的是写作的中断。以前跑车间隙写的稿子陆续被退,附言总说“内容偏激”“逻辑混乱”。躁期写的文字像脱缰的野马,颠三倒四;郁期对着稿纸坐半天,笔尖划出深深的印痕,却落不下一个完整句子。有次截稿日临近,急得满头大汗却一字写不出,把稿纸撕得粉碎时,突然生出想把自己也撕碎的冲动。
家人是锚
妻子悄悄把药片摆成小金字塔,放在我饭碗旁边;我躁期喋喋不休时,她就默默织毛衣,时不时应一声“嗯”;郁期卧床时,她把饭菜端到床头,一勺勺喂我,像照顾孩子。半夜醒来常看见她在灯下缝补衣服,针脚歪歪扭扭,说是白天在纺织厂累的。摸着她砂纸般粗糙的手,眼泪掉在她手背上,她却笑着说:“等晓雯长大了就好了。”
女儿晓雯上小学就学会了察言观色。我情绪不好时,她会把满分试卷递过来;我躁期摔东西,她吓得躲在门后,却在我平静后端来温水:“爸爸,你喝口水会舒服点。”她作文里写“我爸爸是超人,他在跟坏情绪打架”,捧着作文本的我哭得像个孩子,觉得这“超人”当得太窝囊。
2013年冬天,我犯了个致命错误。情绪稳定了阵子,便觉得自己好了,偷偷停了药。第三天躁期就猛烈爆发,我取出全部积蓄说要开公司,在车站和乘客吵架差点动手。妻子把我锁在家里,我却砸碎窗户冲进雪地狂奔,寒风像刀子割脸,心里却燃着莫名的怒火。
警察把我送回医院时,张医生恨铁不成钢:“你这是拿命开玩笑!”妻子在病房外哭红了眼,削苹果的手直抖:“以后别这样了,咱好好吃药,啥坎儿过不去。”苹果的甜涩混着眼泪咽下时,我才懂,接纳病情比对抗它更需要勇气。
在废墟上种花
2020年网约车兴起,莒南至青岛的高铁开始运营,客运生意一落千丈。大巴车常空驶,每月还得还贷款。孙干事暗示要好处费才能保住线路,躁期发作的我拍着桌子吵架,结果线路审核没通过。失去生计的打击让我陷入重度抑郁,把自己关在房间三天三夜,妻子撬开门时,我已经虚弱得站不起来。她抱着我哭:"你要是走了,我和孩子怎么办?"这句话像道惊雷,把我从绝望泥沼里炸了出来。
药费像座大山压着家。妻子去废品站捡塑料瓶,被流浪狗咬了也瞒着,直到伤口发炎流脓。我拿着诊断书去民政局求助,工作人员翻着白眼说“不符合条件”,那一刻觉得自己像粒被遗弃的尘埃。社区帮忙申请的慢性病补助虽不多,却解了燃眉之急,让我明白绝境里总有微光。
王编辑联系我时,客运线路刚被取消。“你的文字里有生活的重量”,他的话让我把出租屋角落改造成书房。写作成了对抗黑暗的武器,却比开车难多了——躁期一天能写五千字,第二天看全是逻辑混乱的废话;郁期盯着空白文档,光标闪得人心慌,半天敲不出一个字。有次为赶稿减了药量,结果躁期发作摔了电脑,硬盘里的稿子全没了。妻子抱着崩溃的我哭:“咱不写了行不行?”我却摇头,写作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。
2021年晓雯考上师范学院,学费成了最后一根稻草。她偷偷找了三份兼职,发传单、做服务员、当家教,被我发现时,手上全是磨出的茧子。“爸,我不念了”,她低头说出这句话时,我一巴掌打在她脸上。这是我第一次打孩子,手心火辣辣的疼,比打在她身上还疼。
裂缝里的光
2022年春天,那本取名《奔跑吧生命线》的稿子终于写完。抱着打印出的书稿,像抱着新生的婴儿,每一页都浸着汗水和泪水。妻子做了碗鸡蛋面,卧了两个荷包蛋当“庆功宴”。投稿过程比写作还难,十几家出版社陆续拒绝,理由大同小异:“题材小众”“没有市场”,最后一家小型出版社也遗憾地回复“风险过高”。
收到最后一封退稿信那天恰逢郁期发作,“暂不采用”四个字让所有坚持崩塌。我把书稿撕得粉碎,妻子没骂我,只是蹲下去一片一片捡起来,用胶带小心翼翼粘好。她的手指被纸划破,血珠滴在稿纸上,像开出绝望的花:"咱再试试,总会有希望的。"
晓雯帮我注册了起点中文网的账号,把粘好的书稿逐字录入电脑。“爸,现在年轻人都在网上看书,说不定有人愿意读你的故事。”她给文章起了个新标题:《与双相共处的日子》,用我的笔名“朽木”发布了第一章。那天在网站后台看到“发布成功”的提示时,我盯着屏幕发呆,没想到十五年的挣扎,最后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发。
连载期间,我结识了一位叫小菁的读者。她也是双相患者,曾在医院里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日夜。小菁刚入院时,情绪低落到极点,对生活失去兴趣,还常因小事与家人争吵。躁狂发作时,她会暴饮暴食、过度消费,而药物的副作用也让她痛苦不堪。但在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,她逐渐好转。小菁在评论区留言:“看到你的文字,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我们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的人,希望能一起找到出口。”
还有一位叫小李的读者私信我。他曾被双相情感障碍折磨得无法正常工作生活,每年2 - 3次的发作频率,让他陷入躁郁与抑郁的循环,多次产生自杀念头。在杭州武林医院心身医学中心的治疗下,他逐渐康复,如今已能全职工作,重建社交。小李说:“你的故事给了我勇气,让我想起自己康复路上的点点滴滴,那些痛苦终将成为过去。”
这些读者的故事激励着我,让我在每一个写作困难的时刻都能坚持下去。随着章节不断更新,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读者群,分享服药心得和生活感悟。有人说:“每天等着看你的更新,成了我生活的动力。”那一刻,所有痛苦和挣扎都有了意义。
现在的我在社区图书馆做义务管理员,每天整理书籍的间隙,会在电脑前写两章更新。“心灵角落”的心理学书籍旁,摆着打印出来的《奔跑吧生命线》手稿,纸页边缘已经卷了毛边。每天吃药时,丙戊酸钠的味道已成生活的一部分,手抖的毛病时好时坏,天气变化会头晕,但我不再害怕别人知道我的病。
晓雯寄来的照片里,她在山区支教,抱着留守儿童站在破旧教室前,墙上贴满孩子们画的太阳。“爸爸,这里的孩子需要光,我想做他们的光,就像你是我的光一样。”看着照片,想起1996年田埂上那个攥着录取通知书的少年,突然懂得,命运给的坎坷里,藏着最珍贵的礼物——家人的爱,文字的力量,与自己和解的勇气。
清晨五点半,我准时起床吃药,窗外的汽车站依旧繁忙。这场与双相的战斗还没结束,未来仍有风雨,但我不再害怕。就像那首歌唱的:“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,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”生命的长途车还在继续,这一次,我握紧了方向盘,也握紧了屏幕那端无数双给予我力量的手。

专家点评:
马辰怡,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,精神科医生,中级心理治疗师
在跌宕起伏的情绪中寻求稳定——致一位双相患者
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,前辈曾教导我们,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。读了这位患者的自述,我被文中细腻生动的描述而打动,信很长,清晰地表达了一路与情绪问题战斗的辛苦与希望,信也很短,比起十余年的人生,信里能描述出来的不过一二。作为精神科医生,很高兴能够获得从患者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疾病的机会,也希望借此回信,让更多的人们理解双相情感障碍,理解受此疾病困扰的人们。
双相情感障碍:情绪的风暴
双相情感障碍(以下简称“双相”)是一种慢性、复杂性的大脑疾病,就像高血压、糖尿病一样,它也有其生物学基础,主要影响大脑中负责调节情绪、精力、思维和行为的神经回路和化学物质,而并非性格缺陷、意志力薄弱或个人选择。
之所以称之为双相,是因为它核心特点就是情绪的“两极摆动”,既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,又有抑郁发作,这些发作并不是普通的情绪波动,而是像风暴一样剧烈的、伴有功能损害的心境发作,通常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。正如患者在信中所描述的,躁狂或轻躁狂发作时异常亢奋,滔滔不绝,手舞足蹈,精力充沛,脑子像装了永动机,各种念头翻涌不息,还会有发脾气、摔东西等表现;而转到抑郁相时,又会感觉坠入谷底,陷入深深的悲伤、空虚、无价值感,精力不足、整天躺在床上,对周围的一切都感觉麻木。患者在这两种极端状态之间切换,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、失控,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恐惧、痛苦以及深深的无助。
二 专业治疗:寻找情绪的平衡
双相情感障碍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通常采用药物治疗、心理治疗、物理治疗等措施结合的综合治疗原则。药物治疗包括心境稳定剂、抗精神病药物,必要时还可以使用抗抑郁药等,控制情绪、预防自杀等,患者提到的丙戊酸钠正是有效的心境稳定剂;心理治疗如认知行为治疗、家庭治疗等,需与药物治疗配合,可以在疾病的不同时期给予患者及家属心理支持、学习调整认知和管理情绪的方法;神经调控技术如经颅磁刺激、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等对急性期控制情绪症状也有确切的疗效;另外还有绘画、音乐、重建规律生活等康复措施可帮助患者逐步恢复社会功能。
三 病耻感:打破心中的枷锁
患者信中说病耻感像件潮湿的棉袄,裹得人喘不过气。在我们的临床实践中,同样发现病耻感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康复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之一,它不仅是内心的沉重负担,更会直接影响患者寻求帮助和坚持治疗的意愿。好多患者都会表现出隐瞒病情、不愿就医、偷偷停药、远离原来的社交圈、持续地否定自己等,一时很难接受生病的事实。
应对病耻感是一个需要患者、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的过程。首先,我们要学会正确看待这个疾病,了解疾病的特点,调整自己的认知:“患上双相情感障碍不是一件可耻的事,勇敢地面对它、管理它,是一件需要力量和勇气的事。”其次,我们可以建立外部的支持系统,比如家人、朋友以及同伴们的支持,有亲友的默默支持和理解,或者与有相似经历的人交流、分享感受,来消除孤立感和羞耻感。就像这位患者,他是幸运的,有爱他的妻子和女儿,也通过写作结识了感同身受的读者,互相给予力量。另外,专注于治疗和康复,按时服药、定期复诊是稳定病情的基石,病情稳定本身就是对病耻感最有力的回击——它证明了你正在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生活。最后,很多患者在历尽千帆之后会通过公开分享自己的感受来消除污名。这不仅能帮助他人,也是自我疗愈和赋能的强大过程,如同这封信一样深刻、令人动容,用文字的力量告诉大家,你并不孤单,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与你同路,并且有许多人已经顺利走出了阴霾,过上了充实、有意义的生活。
四 康复期的小Tips:从控制症状到重新拥抱生活
对于双相患者而言,控制住情绪是治疗成功的一小步,后面更多的是巩固这一阶段性胜利的果实,防止再次复发。核心目标就是规避复发诱因,重建生活秩序,真正实现“从控制症状到重新拥抱生活”的跨越。
第一,规律的生活是情绪稳定的基础,要尽量避免熬夜、日夜颠倒的行为,因为睡眠紊乱会直接打破脑内神经递质的平衡,诱发躁狂或抑郁,同时睡眠不好也可能是疾病复发的重要征兆。第二,酒精、烟草及各类精神活性物质,也会干扰大脑神经递质的正常代谢,成为复发的“催化剂”。还有含咖啡因的浓茶、浓咖啡也可能导致神经兴奋及影响药物代谢,从而影响睡眠和情绪稳定。第三,我们也许无法完全回避压力,但是要学会应对,可以提前制定压力应对预案,比如遇到挫折时及时与家人、医生或病友沟通,避免独自承受;也可以培养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,如运动、绘画、音乐、正念冥想等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绝对不要擅自减药或停药。很多患者觉得“症状改善就是病好了”,悄悄减药或停药,很快会导致复发,再次陷入情绪风暴,甚至某些药物(如丙戊酸钠)的突然停用可能会诱发癫痫等严重后果。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坚持用药、门诊随访,跟医生保持沟通,谨遵医嘱调整药物,才是对患者最安全、最有效的方案。
结语:
感谢患者愿意分享他与双相共处的日子,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在情绪的浪涛中起起伏伏的不易,也以自己的经历为仍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撕开一道裂缝,让希望的光能够透进去。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阅读到这些文字,理解双相情感障碍这一疾病,再遇到情绪困扰时,勇敢地寻求专业的帮助,再遇到受情绪困扰的人们时,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