药没断、罪没少受,10 年抗癌仍失控 ——她为何舍北京赴郑州寻医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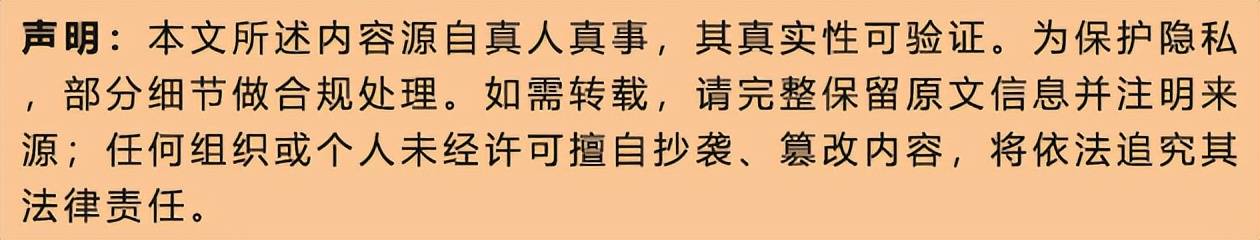
2015 年深秋的体检报告,像一块冰砸进尹阿姨的生活 —— 右侧甲状腺藏着个 406025mm 的肿物,医生的建议斩钉截铁:切除。月底的沧州市中心医院,"左甲状腺切除术 + 右甲状腺癌根治术" 的刀刃落下,病理报告却撕开更狰狞的真相:右侧癌肿已啃噬周围软组织,右中央区淋巴结成了转移灶,连左侧都藏着多发性微小乳头状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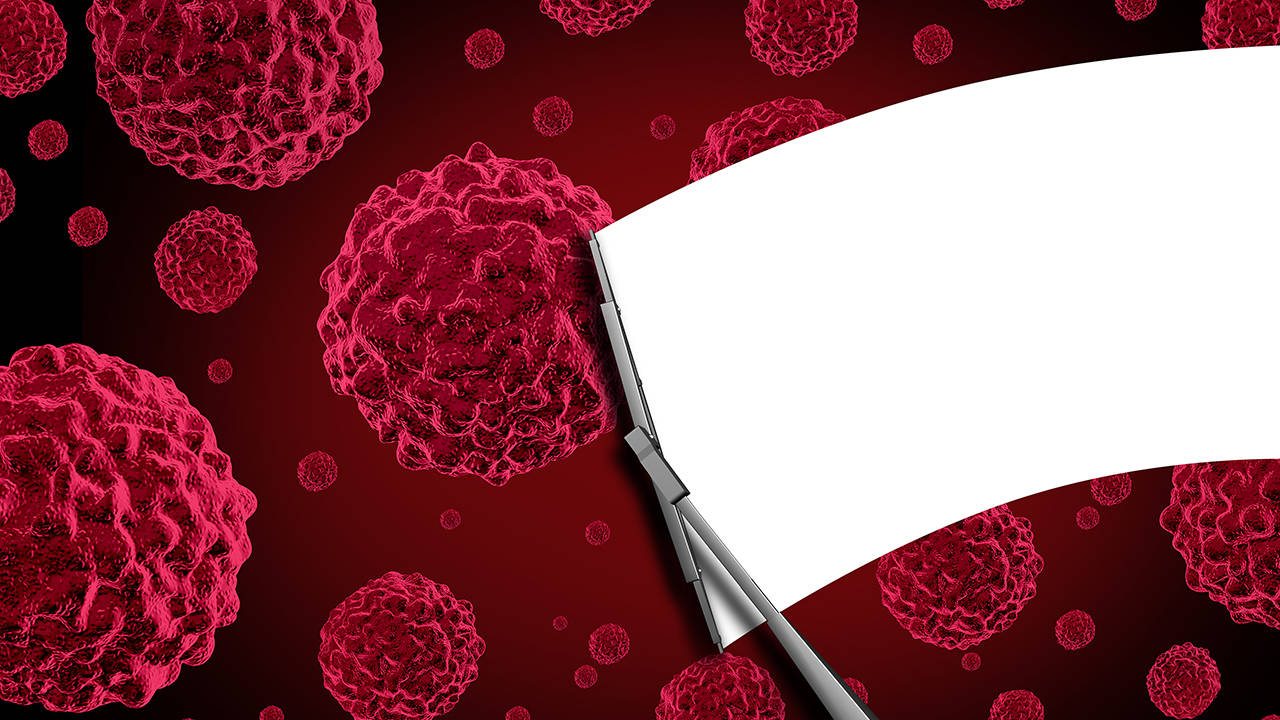
术后恢复得不错,医生说按时吃优甲乐、定期复查就行。一家人攥着复查单走出医院时,阳光透过梧桐叶在地上筛出碎金,他们以为这场噩梦终于熬到了头。
可癌细胞没打算善罢甘休。2016 年清明刚过,复查 CT 的光影里,双肺布满可疑结节,"考虑转移" 四个字像乌云压顶。2018 年深秋的超声图上,双侧颈部淋巴结肿成了鼓包;2019 年霜降时节,双中下颈的肿大淋巴结更嚣张了。尹阿姨对着报告单发愣,手里的优甲乐包装被捏出褶皱:"手术做了,药也没停,怎么就压不住呢?"
2021 年盛夏,天津肿瘤医院的手术室灯光两次亮起,淋巴结清扫术没能拦住病情的脚步。优甲乐的剂量调了又调,身体里的 "叛军" 却越发猖獗。

她开始把希望投向中医。一家人揣着病历本闯进北京,德胜门医院、广安门医院的药汤喝了两三年,直到 2024 年冬,甲状腺球蛋白指标从正常值飙升到 296,像根刺扎进心窝。2025 年惊蛰刚过,CT 片上的阴影更浓了:右肺上叶 15mm16mm 的磨玻璃影虎视眈眈,双肺实性结节最大长到 18mm14mm,纵膈淋巴结也肿成 14mm*12mm 的硬块。
尹阿姨在诊室走廊的长椅上崩溃了。这些年她像捧着易碎品般护着自己,中药西药从没断过,可爬三层楼就喘得像风箱,一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,累得连说话都嫌费劲儿。"我到底做错了什么?" 她抹着眼泪问老伴时,终于想起六年前好友的话 ——"郑州希福肿瘤医院的袁希福院长,看肿瘤特别细,我亲戚就在那儿看好的"。当初总觉得北京的医院更靠谱,如今才明白,救命的药不分地域。
3 月 13 日天还没亮,老两口就揣着大包病历赶到郑州。袁希福院长问诊时,指尖搭在脉上,眼睛却像读透了她的心事:"你这病,跟爱生气、睡不好脱不了干系。" 药方开好,院长的叮嘱像春风拂过:"千万别熬夜动气,天大的事儿,先顾着身子骨。"
5 月复诊那天,尹阿姨穿着新买的碎花衬衫,脸颊透着健康的红晕。"胸口不闷了,肩膀也不酸,袁院长的药比北京的管用!" 她嗓门亮堂,一旁的老伴赶紧补充:"现在一天能走一万步,还敢骑车遛弯,脾气也顺多了。"

袁院长放下笔抬头笑:"活动得循序渐进,可别累着。" 那句带着家长式关切的叮嘱,让老两口对视一笑,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化不开的暖意。
尹阿姨的故事像面镜子 —— 我们总盯着肿瘤大小、指标数字,却忘了那些藏在疲惫里的叹息、困在焦虑中的失眠、堵在胸口的闷气,其实更需要被看见。如今每个清晨,她和老伴骑着自行车穿过街角的早餐铺,晨风中飘来的油条香气,都是失而复得的幸福滋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