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定京济心理科刘洪峰主任详解:“创伤应激障碍”是大脑“警报器关不上”
创始人
2025-11-08 01:21:41
0次
前几天保定京济医院门诊,做销售的张先生来就诊:“半年前出车祸后,一坐车就手抖冒冷汗,晚上总梦到撞车,控制不住。” 刘洪峰主任拍着他的肩解释:“这是应激创伤障碍。”有30多年经验的他,常拿烟雾报警器打比方:“就像报警器坏了,没火情还一直响,这病就是大脑警报器卡壳,危险过了还亮红灯,所以总紧张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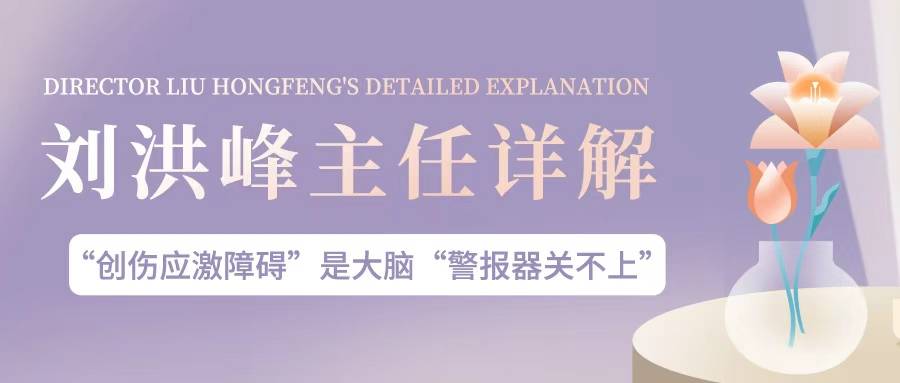
早期信号:这些“不对劲”,是创伤在“提醒”
“好多人觉得‘过阵子就好’,其实早发现恢复快一倍。”刘洪峰主任说,他见过火灾后不敢开燃气灶的大姐,被抢后开着灯睡觉的小伙子,这些都不是“性格变怪”。他提醒家属:若身边人总反复想创伤细节、刻意回避相关人和事,或情绪变暴躁(比如张先生以前对孩子耐心,现在常吼),别不当回事,这是在说“需要帮忙”。

家庭支持:别让“别想了”成“二次伤害”
“家属常说‘别想那事了’,其实特伤人。”刘洪峰主任见过患者跟妻子说梦到车祸,妻子却嫌“晦气”,之后患者再也不倾诉。他支招:先当听众,别打断反复说事儿的患者;不想说就陪做小事,比如买菜、晒太阳;别逼对方“坚强”,说 “难受了跟我说,慢慢来”比讲道理管用。

治疗误区:“能扛过去”会耽误恢复
“不少人觉得‘扛扛就好’,结果越扛越重。”刘洪峰主任见过网约车李师傅,车祸后硬撑大半年,最后不敢出门才就医。他强调:“这病跟感冒一样要治,不是擦记忆,是调警报器。” 比如用认知行为疗法帮患者慢慢适应害怕的场景,必要时用药缓解失眠紧张。“之前有姑娘治疗后,从不敢坐公交到能陪妈逛公园,症状超一个月就赶紧来医院,早治少受罪。”
相关内容
热门资讯
永恒之塔2下载慢/下载不了/下...
永恒之塔2作为经典MMORPG的续作,采用虚幻5引擎打造,支持跨平台联机与自由飞行系统。玩家可在开放...
重庆打造长江上游首个客运“绿色...
“这艘游轮和以前不一样了,没有噪音和油烟,感受到的是江风和两岸的美丽夜色,体验很好。”在位于渝中区的...
原创 阿...
莉莉贝特小朋友最近在迪士尼乐园庆祝了她的四岁生日,现场氛围十分欢乐。照片中的她和阿奇王子一同亮相,成...
周二004非洲杯:尼日利亚VS...
北京时间12月24日01:30,非洲杯小组赛C组首轮迎来一场焦点对决,非洲豪门尼日利亚将迎战坦桑尼亚...
周二002非洲杯前瞻:塞内加尔...
12月23日23:00,非洲杯小组赛焦点战打响,卫冕冠军塞内加尔将迎战“斑马军团”博茨瓦纳。本场对决...
一份安心的孝心答卷:途开心如何...
看着手机相册里,父母并肩站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,笑得像孩子一样的照片,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这不仅...
南都癌症调研:近半患者从不体检...
中国人一生患癌风险高达25%至35%,也就是说,每3到4人中就有1人可能罹患癌症——这是国家癌症中心...
弗拉格告别慢热终于开窍?19岁...
今天,在一场多名状元的混战中,独行侠最终客场惜败鹈鹕。 新科状元郎弗拉格出战35分钟,投篮11中5,...
强直性脊柱炎:别让“强直”锁住...
强直性脊柱炎:别让“强直”锁住你的人生 提到“强直性脊柱炎”,很多人会觉得陌生,但它其实是一种常见的...
